一项新实验突破了我们对拓扑量子物质理解的界限
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进行的新研究正在以高分辨率深入研究复杂而迷人的拓扑量子物质世界——物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可以变形但本质上不会改变的材料的固有量子特性。通过重复京都大学研究人员首先进行的一项实验,普林斯顿团队阐明了原始实验的关键方面,重要的是,得出了新颖而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促进了我们对拓扑物质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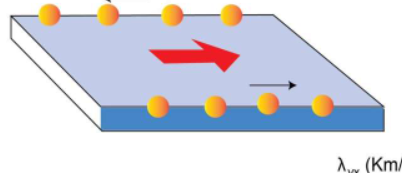
正如发表在《自然材料》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所记载的那样,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一种在氯化钌(α-RuCl3)中实现的特殊类型的磁绝缘体来展示磁绝缘体的第一个例子,该磁绝缘体表现出由量子引起的热霍尔效应在称为Berry曲率的新型力场存在下玻色子的边缘模式。
实验背景
该实验起源于普林斯顿物理学家和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尔安德森的工作,他提出了一种称为自旋液体的新型物质状态。这些磁性材料即使在极低的温度下也不会发生物理学家所说的磁相变。这描述了到一种状态的突然转变,在这种状态下,每个晶格位置的自旋要么以完全平行的模式排列,称为铁磁序,要么以有序的方式在上下之间交替,称为反铁磁序。超过99%的磁性材料在冷却到足够低的温度时会经历这种相变。安德森建议使用术语“几何挫折”“来描述如何防止自旋液体发生这种相变。
普林斯顿大学EugeneHiggins物理学教授N.PhuanOng说:“为了说明这个概念,想象一下,根据规则,每个女人都应该坐在两个男人之间,反之亦然,试图让情侣围坐在餐桌旁。”论文资深作者。“如果我们有客人一个人来,这种安排在几何上是不可能的。”
2006年,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的俄罗斯物理学家AlexeiKitaev提出,无需援引安德森的几何挫折概念即可实现安德森的自旋液态。他用一系列优雅的方程式概括了这一点,重要的是,他预测了称为Majoranas和visons的新粒子的存在。Majorana粒子是一种特别奇怪且难以捉摸的亚原子粒子,它于1937年由意大利物理学家EttoreMajorana首次提出理论。它是一种费米子;事实上,它是唯一被认为与其自身的反粒子相同的费米子。
Kitaev的工作引发了一系列研究,以寻找可以在实验室中实现他的模型计算的材料。两年后,德国斯图加特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两位物理学家GeorgeJackeli和GiniyatKhailyulin预测氯化钌(α-RuCl3)最接近。这种以蜂窝状晶格结晶的材料是一种极好的绝缘体。
因此,在过去十年中,α-RuCl3已成为量子自旋液体研究最深入的候选者之一。2018年,物理学家松田雄二及其京都大学的同事报告了对Kitaev计算中预测的“半量化”热霍尔效应的观察结果,这项研究得到了相当大的推动。
热霍尔效应类似于更熟悉的电霍尔效应,它描述了强磁场如何使施加的热流向侧面偏转。侧向偏转会在样品的两个边缘之间产生微弱的温差,如果磁场方向反转,则温差会反转。虽然热霍尔效应在铜和镓等金属中得到了很好的证实,但在绝缘体中却很少观察到。Ong指出,这是因为在绝缘体中,热流是由称为声子的晶格振动传递的,声子对磁场无影响。
Matsuda报告说,他们对霍尔热导率的测量表明它是“半量子化的”。正如基塔耶夫预测的那样,大小仅取决于普朗克常数和玻尔兹曼常数,与其他无关。“这个实验意味着对马约拉纳粒子流的观察,引起了社区的极大兴趣。”
但是长期熟悉热霍尔实验的Ong和他的研究团队认为Matsuda的结论有些不对劲。“我不能完全把手指放在上面,”Ong说。
本实验
Ong和他的同事们决定重复这个实验。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在更高的分辨率和更大的温度范围内进行实验——从二分之一开尔文到十度开尔文。
论文的第一作者、物理学研究生PeterCzajka解释说,高分辨率对于实验的成功至关重要。“我们的实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在概念上很简单,但在实践中却非常困难。测量某物的电阻相对容易,但测量样品的热导率要困难得多。”
实验的第一部分要求研究人员选择具有多种特定特征的氯化钌样品,包括具有独特六角形的非常薄的晶体结构。然后他们附上灵敏的温度计来测量温度梯度。
“我们真正做的只是测量晶体上非常小的温度梯度,”Czajka说。“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千分之一到百万分之一度的分辨率——介于这个尺度之间的东西。”
研究人员将材料冷却至1开尔文或更低的温度,并将样品置于与热流平行的强磁场中。然后他们使用电加热器加热晶体的一个边缘并测量温度梯度。令人惊讶的是,这项实验——测量温度梯度——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样品冷却了大约六个月,”Czajka说,“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彻底绘制了温度和场依赖性。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大多数研究人员不愿意将六个月用于单一实验。”
研究人员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热霍尔效应的存在,这与松田的发现相似。当温度计检测到热流的流动根据磁场偏向一侧或另一侧时,研究人员意识到了这一点。
为了解释这一点,Ong使用了顺流而下的木筏的类比,河流象征着热流,木筏象征着一包热熵。“虽然你顺着河流的方向前进,但你发现你的筏子被推到河的一侧,比如左岸。所有跟随你的筏子都同样被推到左岸,”他说说。这导致左岸温度略有升高。
Ong说,该信号对磁场的方向也很敏感。“如果你在磁场方向反转的情况下重复实验,你会发现所有仍在顺流而下的筏子都聚集在右岸。”
在绝大多数绝缘体中,这种效应不会发生。“筏子不会堆积在左侧或右侧;它们只会顺流而下,”Ong说。
但在这些新的拓扑材料中,效果是惊人的。其原因是因为一种称为贝瑞曲率的现象。
原则上,所有晶体材料都显示出一种称为Berry曲率的内力场,该曲率以布里斯托大学的数学物理学家MichaelBerry的名字命名。浆果曲率描述了波函数如何在动量跨越的空间中扭曲和转动。在磁性材料和拓扑材料中,Berry曲率是有限的。它作用于带电粒子,如电子,以及中性粒子,如声子和自旋,就像强磁场一样。
“Berry曲率是一个在过去60年中缺失的概念,但在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现了,”Ong说。“正是我们在这篇论文中证明的BerryCurvature,实际上是松田实验观察的原因。”
同样重要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无法证实马祖达实验中最初预测的马约拉纳费米子的存在。相反,研究人员将热霍尔效应追溯到另一种粒子,即玻色子。
自然界中的所有粒子要么是费米子,要么是玻色子。电子是费米子,而光子、声子和胶子等粒子是玻色子。玻色子起源于高磁场下磁矩的波状集体激发。如果使用的材料本质上是拓扑材料,则这两种类型的粒子都会产生热霍尔效应。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相当有说服力地证明观察到的粒子是玻色子而不是费米子,”Ong说。“如果京都小组是正确的——如果粒子被确定为费米子——信号将与温度无关。但事实上,信号强烈依赖于温度,它的温度依赖性非常精确地对应于拓扑的定量模型玻色子激发。”
“我们的实验是所谓的显示量子边缘传输的玻色子材料的第一个例子,”Ong补充道。
意义和未来的研究
Ong和他的团队相信他们的研究对基础物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的实验通过阐明玻色子而不是费米子的存在而完成的是打开使用热霍尔效应的大门,就像使用量子霍尔效应来揭示许多新的量子态一样,”Ong说。
Ong还表示,在像这样的实验中发现的粒子可能在拓扑量子计算或量子设备等方面具有实际应用,尽管实现此类突破可能需要20年或更长时间。Ong和他的研究实验室的成员打算通过在相关材料中寻找类似的玻色子霍尔效应来继续他们的研究,并更详细地研究氯化钌的量子可能性。这些实验是与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田纳西大学、东京大学和普渡大学的科学家合作进行的。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










